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3年10月5日13:00(北京时间19:00),瑞典学院将20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挪威剧作家约恩·福瑟(Jon Fosse),以表彰他“创新的戏剧和散文,为不可言说的事情发声”。
本期译者专访栏目带各位走进邹鲁路、李澍波两位译者眼中的福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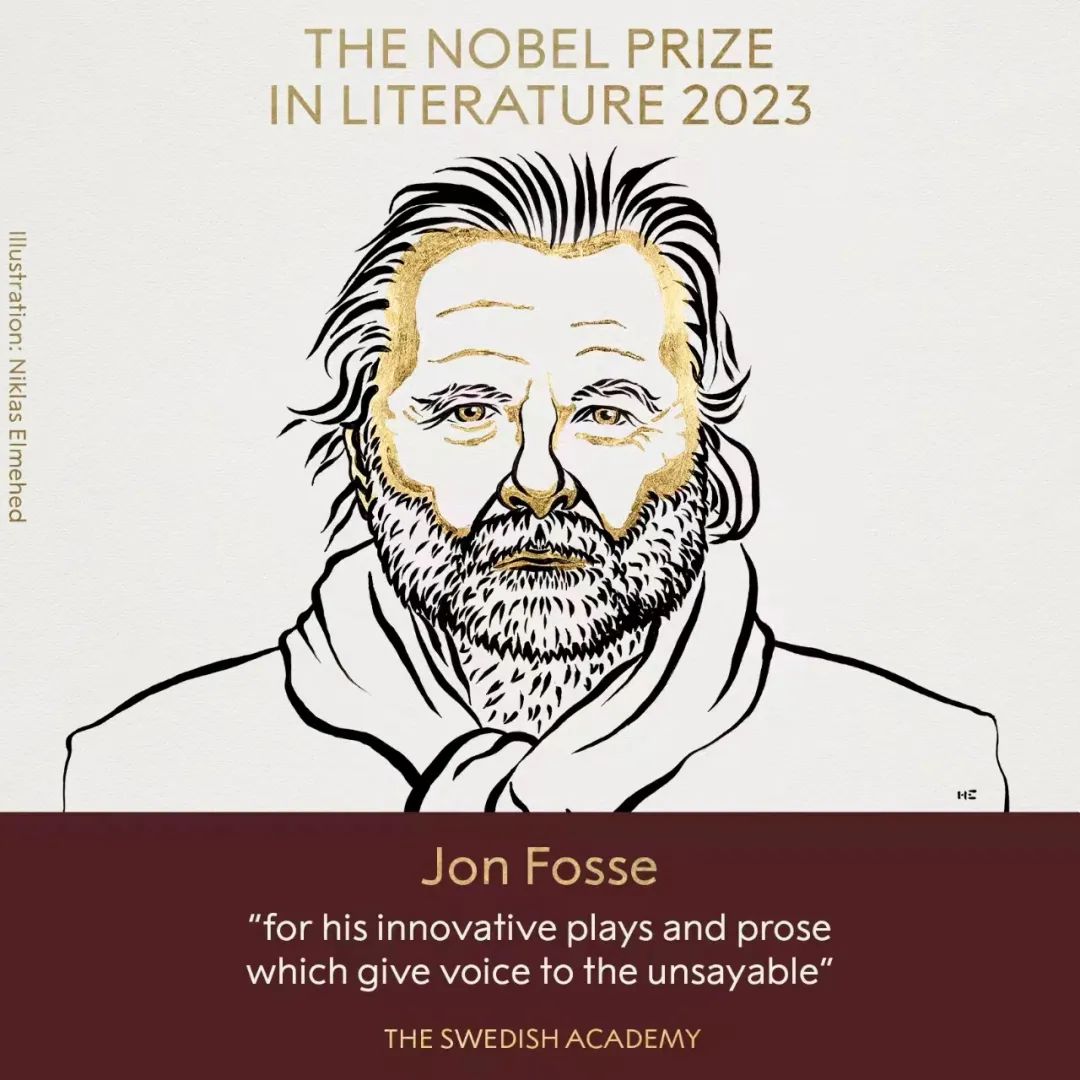
2014年,约恩·福瑟的剧作首次被翻译成中文版,书名为《有人将至:约恩·福瑟戏剧选》,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澎湃新闻当时专访了该书译者邹鲁路。邹鲁路说:“中国戏剧界应该要知道世界戏剧在发生什么。”
澎湃新闻:怎么会开始接触福瑟的剧本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的?
邹鲁路:第一次读到福瑟的戏剧是2003年,我们学校曹路生老师拿到了《有人将至》的英文剧本,觉得很特别,就拿来给我希望能翻译成中文。我当时读完,就感到他的戏剧太不一样了,当时砰一下,我的心就被击中了。我感觉他把人一辈子想说的话都说完了。这种感觉好像有一个石头,从非常远的地方,从挪威又远又冷跟我们国家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地方砸中了我,砸中我心灵中最黑最深的那个地方。在我的人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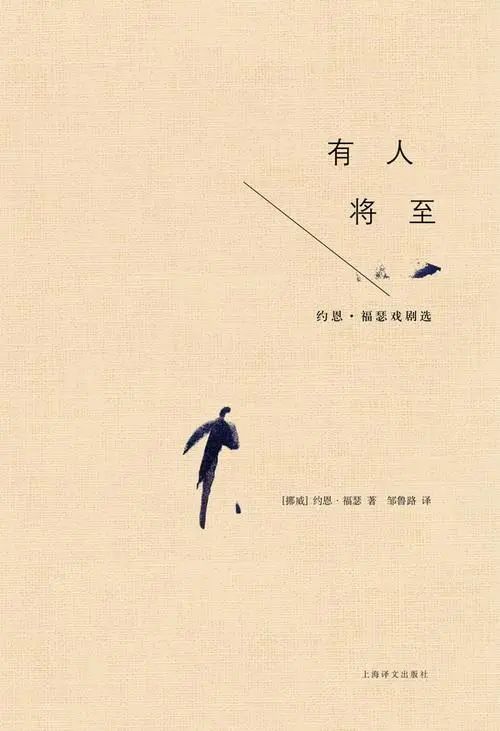
《有人将至:约恩·福瑟戏剧选》
我觉得非常神奇,像福瑟这样的剧作家并不是女性。男性能够通过文字来打动我,到这样的地步,我觉得这是非常神秘的。
自从我的心被巨石击中碎成片片之后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,因为震动太大,我甚至不敢再看这个剧本。我把它扔到抽屉里锁起来,锁了三个月。三个月之后曹路生老师逼我交稿,我才把它拿出来翻译完,就这样发表了。
澎湃新闻:所以你从此开始了长达11年的翻译工作?
邹鲁路:2009年的时候,当时我已经翻译完了5个半福瑟的剧本。那一年我去了挪威参加了卑尔根国际艺术节。那一年也正是福瑟50岁生日,挪威政府特地为他举办了“福瑟50”的主题活动。我在卑尔根呆了14天。14天里下了12天雨。我在雨天去拜访了福瑟先生,看了完整的福瑟作品演出,参加了各种咖啡朗读会。我当时就下定决心,一定要让更多中国人了解福瑟。那一年秋天我遇到了Inger,我和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要在中国做一个福瑟戏剧节。5年过去了,这一次可以说是梦想成真。
澎湃新闻:福瑟是用挪威语写作的,你的翻译是从英语剧本翻译过来的?
邹鲁路:是的,我所有的剧本都是转译的。在挪威有两种官方书面语言形式,一种是“书面挪威语”,一种是“新挪威语”,福瑟写作使用的是“新挪威语”,这个语种非常小,它主要在挪威的西海岸,覆盖人口大概是挪威人口的10%到15%。但是它具有更强的节奏性和动作性,这也是剧作家福瑟选用这种语言的原因吧。
在我翻译福瑟剧本之前,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英国英语版本,后来又有了美国的英语版本。其实福瑟本人也是个非常专业的英语翻译,他翻译改编了大量英语经典。他自己对英语版本也是非常满意的。
虽然中文版都是从英语转译而来,但是优势是这些年我始终和作者保持着直接交流。福瑟先生一直和我通信往来,关注着中文版翻译的进程。
澎湃新闻:就你看来,福瑟在西方世界赢得如此之大的尊重和推崇的原因是什么?
邹鲁路:我感觉他应该是西方世界在世最伟大的剧作家了,据说他现在西方世界被搬演作品的数量仅次于莎士比亚。他的作品得过40多个国际大奖。但是中国人知道他的非常少,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,也是希望中国戏剧界应该要知道世界戏剧在发生什么。
我一直说福瑟的作品介于“云和泥之间”,他的对话非常简短、日常,这和契诃夫很接近;但整个作品却又是极简抽象的,有着荒诞派的特质,和贝克特相似。所以有人说他是新贝克特、新易卜生、新品特。但其实都不能完全概括他。
真正使福瑟成为一个戏剧家而不朽的是他具有鲜明个人烙印的“福瑟式”的美学与戏剧风格,那种蕴含着强大情感张力的极简主义语言,对白中强烈的节奏感与音乐感,并置的时空,交缠的现实与梦幻。另外就是福瑟作品中有着无处不在的诗意。我觉得福瑟首先是个诗人,其次才是个剧作家、小说家、翻译家。
福瑟作品之所以会被反复搬演,是因为他的作品有着普世性。他的作品是非常挪威的,峡湾、风雨、乡村,人与人之间的疏离,看上去它就是在那样一个世界里的。但是非常奇妙的是,在上海这样人与人熙熙攘攘的环境里,这种孤独感,却是相通的。
澎湃新闻:福瑟的剧作本身没有戏剧冲突,很多人会感觉到无聊,西方世界是否也有这样的感受?
邹鲁路:当然。即使在挪威也有很多人不喜欢福瑟,觉得他是个“神经病”,因为他反反复复地说那么几句话。一直在重复,很无聊。
我觉得对于福瑟的戏剧,一定是有他特殊的观众的。一定是经历过人生的人才能读懂它。有时候,他确实把一句话重复了30遍,但其实每一次重复都是不同的,只是你没有听出来而已。我想,对于福瑟是没有中间地带的,要么很爱他,要么讨厌他。一定是这样的。
澎湃新闻:但是福瑟的剧本确实对舞台呈现提出了挑战。
邹鲁路:是的。就像这次福瑟戏剧展,有5个不同国家的作品,但几乎每个导演都说到排练过程中有一个放弃的过程。它确实会把导演逼疯,因为福瑟的作品里没有通常的故事和冲突。他的作品是一首诗,你怎么在舞台上演一首诗,这真的很难。但当你懂得的时候,它是无与伦比的。
澎湃新闻:有些时候,演员甚至不能完全读懂剧本。
邹鲁路:福瑟的戏对于演员的挑战太大了。尤其对于语言节奏的把握。2010年福瑟的戏剧在上海演出《有人将至》的时候,一开始我们剧中的男一号看了一遍剧本说太容易了,然后看到第三遍的时候就开始明白这个戏多难排了。我经常觉得,福瑟的作品是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,比言语更重要的,是言语之间的沉默。
福瑟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不多,他的《三部曲》中文版即将出版,译者是李澍波。李澍波在福瑟获奖的第一时间接受了潮新闻采访。“这个奖,福瑟已经等待22年了。”李澍波说,从2001年起,就有福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了。同时,福瑟这次获奖,对于挪威这个国家来说,也是时隔95年再获奖。(上一次是1928年西格里德·温塞特获此奖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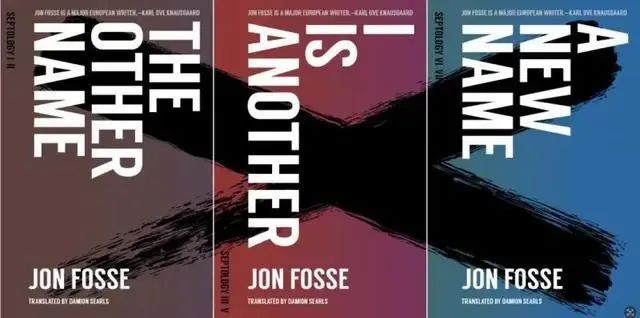
Q:如何理解福瑟这位作家?
李澍波表示,福瑟被广泛认为是“新易卜生”,是挪威继易卜生之后的又一位世界级大作家。他的作品被搬上舞台也是最多的。福瑟在挪威的地位很高,很长时间里享受着写作奖金,享有荣誉住宅——保证了他稳定的收入。此外,他的创作力也非常惊人,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新书,仅剧作就有70部,真正的著作等身。在她的印象里,福瑟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,她最近一次见福瑟,是几年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,福瑟在台上谈新书《九部曲》——这部作品用很长的篇幅写一个人的24小时,是慢小说的概念。
Q:李澍波是如何接触到福瑟作品的翻译的?
翻译福瑟之前,李澍波最早翻译的是福瑟的学生卡尔·奥韦·克瑙斯高的作品——自传体小说《我的奋斗》的第五部《雨必将落下》和第六部《终曲》,2021年、2022年陆续出版。翻译了福瑟的学生的作品之后,李澍波接到邀请,翻译福瑟的作品《三部曲》。这是福瑟2007年到2014年间完成的作品,目前翻译工作还在进行中。
Q:翻译福瑟作品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什么难点?
在李澍波看来,福瑟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的运用,充满大量的实验戏剧的独白。福瑟在语言上力图去文学化,这也是翻译的一个难点。比如福瑟用的是“文盲”的语言,但是表现出的是哲学的意味和思考。如何在中文里找到对应的表达,完美呈现原文的味道,对李澍波来说最费思量。
Q:如何理解福瑟的作品?
理解福瑟及其作品,媒体报道中提到了他是新易卜生,受到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的影响。在李澍波看来,福瑟在写作上受到贝克特的影响更多,包括精神上、表达方式上。而“新易卜生”的称呼,则是因为他作品的数量和影象力。“但福瑟本人的风格也是多样的,写作也先后经历过几个阶段的变化,现在的他更深沉、更收敛。”李澍波说,“对他这样原创能力极强的作家,很难以一位前人作注释。”在写作之余,上世纪90年代,福瑟还在挪威西海岸城市卑尔根牵头成立了一个写作学院。这是一个教授创意写作的学院,出版过或没出版过作品的写作者都可以提交申请加入。这个学院已经培养了很多新一代作家。在福瑟看来,写作是一个可以传授的技艺,多年来,他也不断创新教学方式,比如带大家一起读诗等。
文章来源:澎湃新闻、钱江晚报
